1、春天山野上开满了烂漫的花朵,像海浪一样席卷了整个山头。温凉的风儿在花丛中把花香酿成的酒,一杯接一杯地喝下去,一批接一批地从那...

1、春天
山野上开满了烂漫的花朵,像海浪一样席卷了整个山头。温凉的风儿在花丛中把花香酿成的酒,一杯接一杯地喝下去,一批接一批地从那温柔乡里踉踉跄跄地走出,憨笑着,到处跌跟头。
流浪成性的风儿,把整个山头都沾染上了浓烈的花香,风情似那花香般饱满,似要吸引我们也去大醉一场。


天空从沉睡中醒来,洗净了脸,露出那象牙白的肤色。
我梳洗好后,披上大衣,倚在窗台前,看着几近要探入屋内的白花。花朵的雅白上调和了天上掉下来的灰白色脂粉,像朦胧的清晨一样,教人昏昏然。时候还早,花儿还酣睡着,泡在露珠中,吸收着天地灵气。
“在做什么?”意儿轻轻地撩开珠帘,走了进来,顺着我的视线,往外探了探。她把火点着,烧了一壶水,在旁边的木桌上,把茶具铺开,熟练地泡着茶。我躺在榻子上,微闭着眼,懒散地感受着早上的凉风在我温热的皮肤上蒸腾着,搏斗着,从那忽冷忽热的感受,便可预见它们在战场上撕杀得有多么激烈。
天空终于开始往脸上涂抹鲜艳得热烈的脂粉了,外面的花儿也跟着沾了光,个个从露水里探出娇嫩的花瓣,着上艳丽的色彩,一派雍容、梳懒的模样。


来到了院子门口的田地里后,在开始耕作前,我摸了摸干燥的泥土,是那么的朴素、厚实,令人心安。田地就像一件原材料一样,任我发挥,把它制成一件艺术品,最后的粮食就是它的价值。艺术品太宏大,要做的东西很多,除草、犁地、开垄……
我和意儿一年前逃到这里,要想生活下去,还是得有足够的粮食,才能保住现在安稳的生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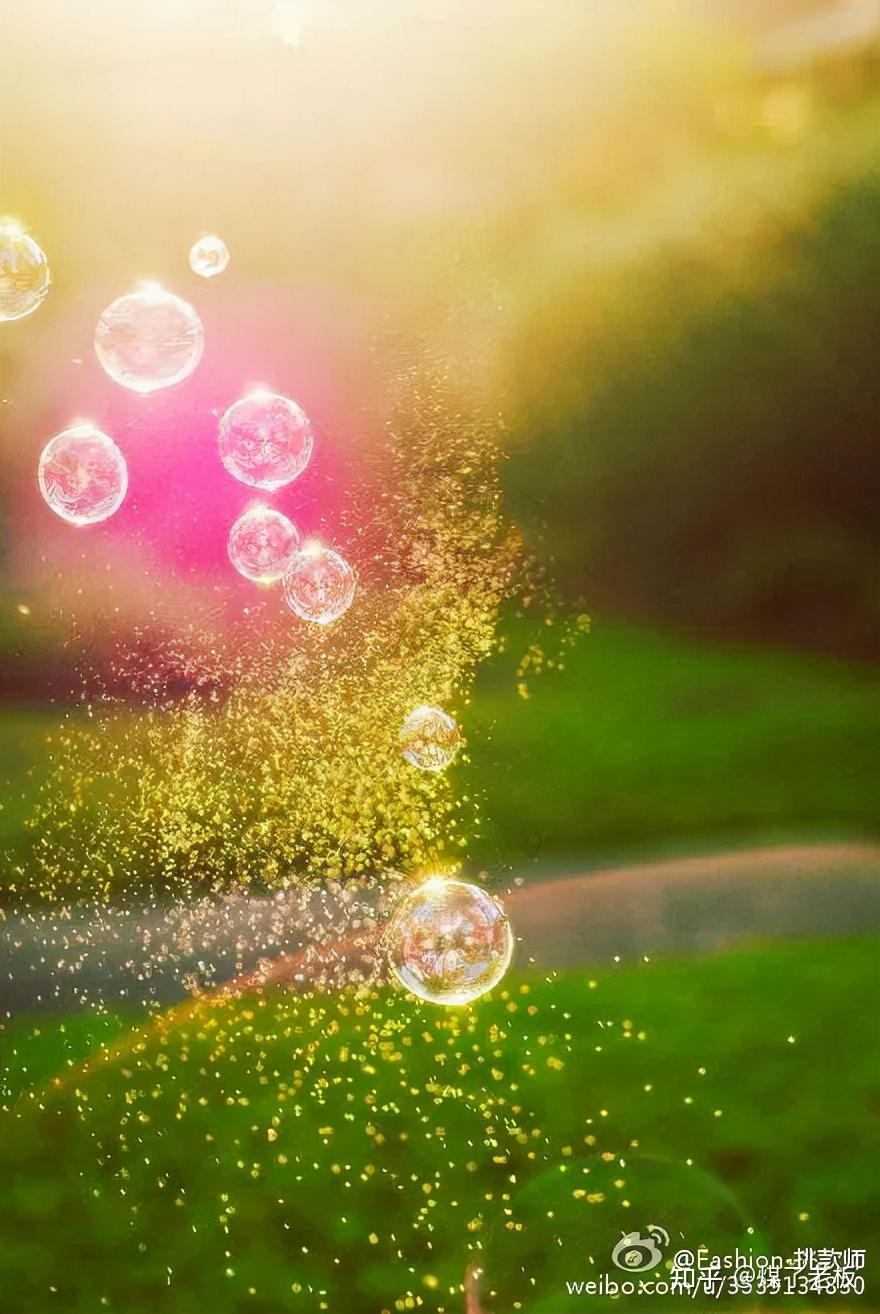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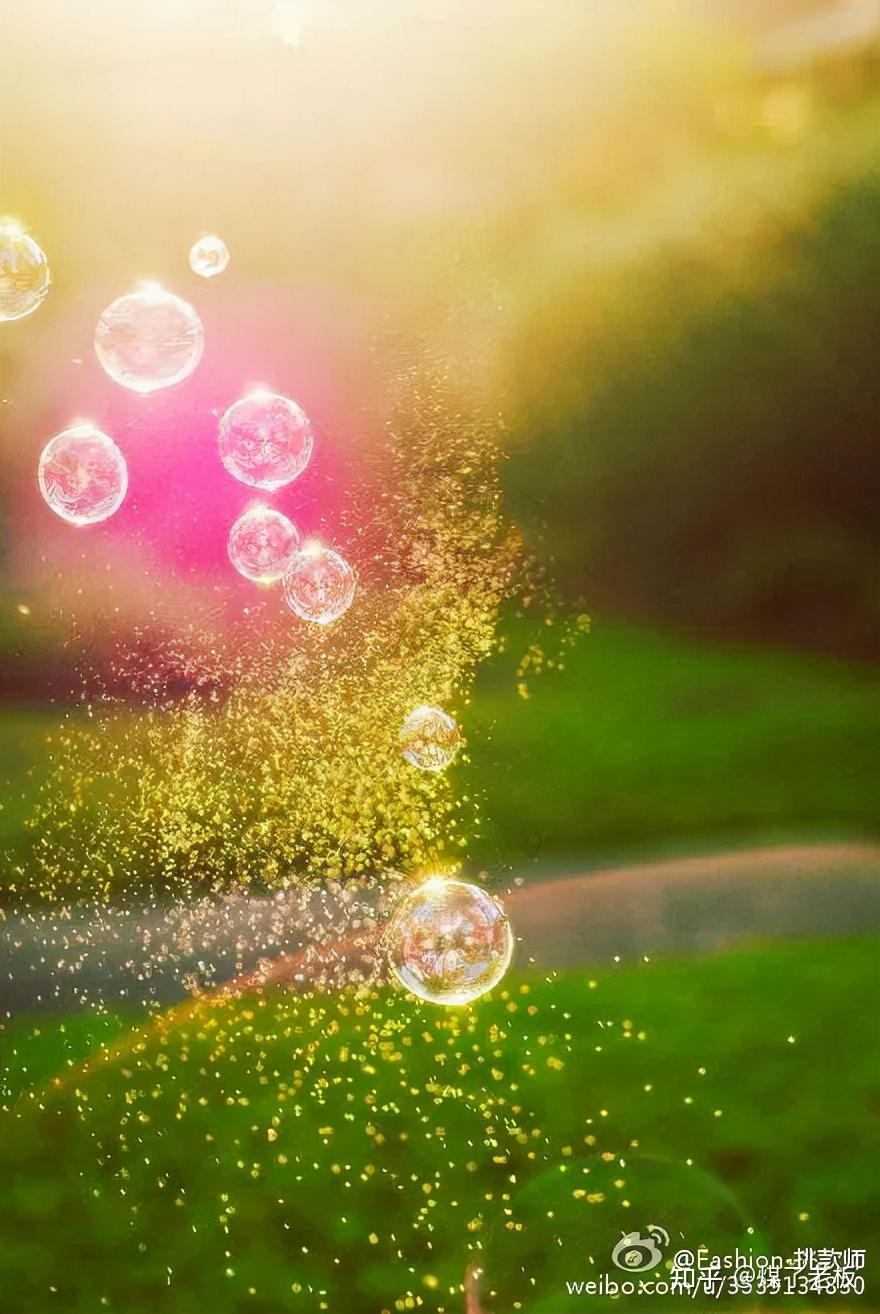
日近中午了,太阳晒得地上的植物出了汗,除了谷物发甜的香味外,还有略微刺鼻的青草味在空气里悄悄地染了个角。
不远处,意儿晾上的衣物、被单在阳光下被风鼓起,像朵花似的明媚、清新。
我拿起脖子上的汗巾,把脸上的汗揩去,看着自己逐渐规整起来的田地和那已经下了地的苗子,似乎一下子就可以看到丰收时的我,在一筐一筐地往家里抬着粮食,把那放粮食的房间堆满。像钱让他们如此着迷一样,那成屋的粮食带来的安全感也让我感到迷醉的满足。
2、夏天
金黄的阳光被植物割碎,洒了满地的碎片,还有大片大片完整的阳光搁在上头,摇摇欲坠。院子里的架子上爬满了绿色的藤蔓,它们小心翼翼地护着怀里那一方鲜嫩的、温凉的空气。旁边大树上知了的叫声闹哄哄地在山野里翻涌着,像一群无所事事的混混满大街地乱跑、乱叫。


意儿摘了好些果子回来,我打了几桶冰凉的井水上来,把果子放里头冰着。下午的热气已经消散了好些,吃过晚饭后,我坐在门口摇着蒲扇乘凉,意儿在水井边洗头。
我看着夕阳底下,那细碎的光片沾在她的湿发上,随着她的动作扫来扫去,还有那微弱的皂角香在空气中氤氲开来。她像一捧清水一样,似乎下一秒就要消失在那飞溅开来的井水里。


晚上天黑了以后,我坐在如豆的灯苗前看书,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,像一个猎人一样,尽情地捕捉着、编织着脑海里的灵感,想要把它们全部都吐在沾满黑墨的笔下。意儿在拿着针线活在做着,偶尔她眼累了,我还会帮她穿一下针线,让她得空休息会,顺便听听我写的文章。
屋外的蛙鸣像涌浪一样,一阵一阵地往屋里翻涌着。整个世界似乎只剩下了我们这一方质朴的生灵在努力地生活着,感受着生命纯真的热烈。


3、秋天
晚上睡觉前,我没有关窗,早上太阳还没有出来,凉风已经卷着枯叶送到了我的枕边,轻轻地呼唤着我。我拿起长长的扫把,心无杂念地、虔诚地清扫着门外的落叶,偶尔累了,也会停下,伸出手抓住在空中飞舞的那一张落叶,像花儿一样捧在手心,放在心口处。它只是换了个颜色的衣裳而已,我能感受到它的生命仍然在那错落的筋脉里流转。
意儿已经在院子里头忙活开来了,她在准备一些腌菜和腌肉,在下雪天时,那可是顶好的美味。时候不早了,我得上山去拾柴,得准备充足的柴火来度过寒冬。我走在高大、结实的森林里,偶尔也会原地顺滑地转个圈,看着落叶随着衣裙在脚底处旋出不同的花儿,但那只是我烂漫的心情展现出来的冰山一角。


柴火很重,我累到气喘吁吁,心跳声像擂鼓一样,在静谧的山林里,激烈地敲打着我的耳膜。我的血液一股一股地涌上我的大脑,像我现在的生命一样,热烈地释放着热情,滚烫得要将我融化在生活的喜悦里。
4、冬天
冬天即将过去,寒气像被扔进了锅里一样,不断地被热气侵吞。白色的积雪也逐渐从地表隐退,露出湿漉漉的泥土。
意儿还在床上微弱地昏睡着,脸色像死了苍白。她生了重病,我知道我救不了她,我们逃离外面的世界,却又被困在心里的世界。我走不出这里,别人也走不进来,外面也许会有一丝希望可以救她的命,但我们已经成为异类了,异类又怎能在那紧得要让人窒息的距离里生存下来?


这一天我起得特别早,出去,摘了好些花,还把门外的积雪扫了干净。屋子已经被我收拾齐整,所有的门都打开了,到处都洒上芳香的花瓣,它们在风中温柔地席卷了屋子的每个角落。我帮意儿梳洗好后,为她穿上她最喜欢的衣服,而后,我才开始把自己料理干净。
天色已经昏黄了,我点燃火堆,煮了一壶茶,把意儿从床上扶起来,坐到桌边,刚好可以看到外面灿烂的晚霞,她摸了摸我的头发,脸上露出了粉红的笑容,不知是夕阳的余辉,还是她翻滚上来的血色。我陪着她一直坐着,呆呆地看着太阳,直到它的底儿触碰到了模糊的山峦。我深深地看了意儿一眼,吻了吻她淡红的眼角,站起了身,把煮茶用的火堆,勾出到旁边,那里有倾洒了一地的火油。


熊熊大火像热烈的生命一样四处地张扬着、吞噬着,我笑了,意儿也笑了,我们的眼睛已经被大火引出了几行热泪,那透明的泪水,像我们的生命一样,不断地流逝,不断地变红,不断地流逝……










如果认为本文对您有所帮助请赞助本站